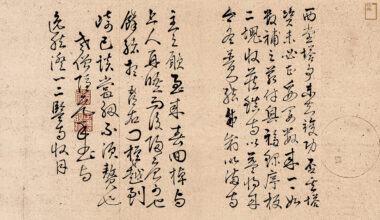越過波蘭東部邊界,一踏上烏克蘭國境時,你便已抵達主要大城,利沃夫(Lviv)。第一眼打量利沃夫,你幾乎渾然不覺這是個深陷戰火的國家。帶著幾分驚喜與迫不及待的熱情,瀏覽城內被列為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」世界遺產後,你開始意識到,實情不若你想像的單純。比方說,好幾座老舊雕像與公共藝術作品都被厚重的油畫布層層包裹,底部則有沙袋包圍,那不是修復或重建,而是重重保護。警覺性立即提升,你開始和周遭的人們攀談,定睛注視他們的眼神,節制的笑容與客氣的言行背後,有些事不太對勁。
「那些事」,不但很快令你赫然了悟,而且讓你親身體驗——當你準備就寢時,冷不防被一陣空襲警報驚醒,催促人人跑到離你最近的安全庇護地。經過幾次有驚無險的避難歷練後,你開始像當地人,逐漸習慣警報器的聲響,選擇排除「敵軍可能即將在你數步之遙的距離內投下飛彈」的想法。你若無其事般倒頭再睡;如果是白天聽到警報大作,你可能見怪不怪,神色自若地把飯吃完,咖啡照喝,繼續聊天:漫不經心又無動於衷,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以不屑一顧的冷漠,作為抵抗的唯一方式。
不過,還是常有錯估形勢的時候,在錯誤的時間,出現在錯誤的地方。利沃夫外圍郊區曾幾次遭飛彈襲擊,我好奇遠方某位按下砲彈射出的士兵,是否對亟欲攻擊之城毫無所知?一座又一座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代,以及備受新古典主義影響的建築、樓閣亭臺擠滿歷史城區的天際線——慶幸的是,至今為止,這些建築仍安然屹立。事實上,利沃夫更早以前便已飽經大時代的戰火摧殘而歷劫歸來,除了兩場世界大戰之外,還有其他大小衝突,慶幸的是,這座城市都毫髮無損,整個利沃夫就是個倖免於難的紀念標誌。
亂世下的如常生活
城裡的電車,是老蘇聯時代遺留的舊物,在鵝卵石街道上蜿蜒前行,它們明確清晰的聲音,與超乎預期的準時,完美詮釋一座古意與現代感兼容並蓄的城市。利沃夫的革命廣場是市中心的主要標的,而老猶太聚落已改頭換面成時髦餐廳與咖啡館。城裡獨樹一幟的教堂建築,不分宗派,對外開放讓信徒自由入內敬拜。歌劇院也沒閒著,夏季表演節目與音樂會熱鬧登場,令人驚訝的是,大部分的場次都已被搶購一空。利沃夫市民似乎已學會如何在煙硝密布的亂世下享受人生。咖啡館裡人滿為患,餐廳、酒吧從白天到夜晚人聲鼎沸,公園不乏悠閒散步的人,也有不少人走進燈火通明的百貨公司逛街。街頭藝人吸引人潮圍觀,其中不乏衣著體面的群眾,他們手執最新型的蘋果手機,對著小孩拍照。從表象看來,與預期中「歐洲最貧窮國家」和「全面性戰爭持續進行四個多月」的想像,落差甚大。
炎炎夏日,晚上十點的利沃夫,依舊風暖日麗,驕陽似火。十一點,宵禁準時開始,如常生活暫告一段落,一直到隔天清晨六點前,嚴禁居民外出。萬籟無聲,只有空襲警報偶爾劃破寂靜。
我動身往東部的伊凡-法蘭科夫(Ivano-Frankivsk)前進。眼前一望無際的稻穀禾田,貢獻全國75%的經濟收入,糧倉美譽,名不虛傳。鬱鬱蔥蔥,漸層的金色與綠色稻浪,在藍天下風吹草動,令我想起著名義大利電影《一九○○》。走在如此恬靜的田園風光裡,殺氣騰騰的戰爭似乎遠離,尤其對忙碌的農夫而言,他們無暇關注戰事。粗糙的雙手與肌膚明白地告訴你,農耕早已將他們磨練得不怕艱辛不怕苦。幾位農夫正著手為牲畜準備飼料,我駐足與他們談話。聊起石油短缺,再這樣下去,恐怕拖拉機與收割機也無法發動了吧。若然,莊稼無法採收的風險相對提升。但比較烏克蘭其他地方連稻穀播種的機會都因戰役而未果,他們已屬幸運。雖然未來充滿不確定性,他們仍面帶微笑,認分地埋首持續工作。
煙硝城外的田園生活
農業產力貢獻烏克蘭75%經濟收入,穩坐歐洲糧倉的寶座,其中小麥、穀物油籽產量排名世界數一數二。戰事爆發,俄軍封鎖黑海,成千上萬噸小麥等農產品出口不得,不僅牽動世界原物料供給,也引發燃料危機,一旦拖拉機與收割機無法發動,則提高採收的不穩定與風險。牧場酪農雖不怕產品滯銷,卻擔心石油短缺使現代化機械無法正常運作。
烏克蘭人的民族性堅毅,即便危難當頭,仍不輕易放棄。作為俄羅斯、甚至全歐洲的糧倉,成千上萬噸的小麥至今仍因俄羅斯封鎖黑海而鎖在倉庫裡出口不得。不過,情勢開始有轉機。烏克蘭位於黑海的蛇島,原先遭俄羅斯軍隊占據,但俄軍最近已被驅離,看來,互惠互利的商業貿易,可望於近期內的某個時候恢復往來,將麵包重新放置於歐洲、中東與北非等地的餐桌上。
自從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布「特別軍事行動」(也被稱為「戰爭」)以來,交戰場域已逐漸轉移至烏克蘭東部與南部,首都基輔(Kyiv)已幾乎回到常軌。除了全國性的失業率高居10%,以及停滯的薪資仍未改善,放眼望去,咖啡館與餐廳一如以往地座無虛席,大部分人也一如以往地通勤上下班。當然,有些部分是回不去了,譬如大部分青壯年得參與保家衛國的軍事行列,許多年輕生命為此捐軀殉國,這些青壯年的葬禮是全國各地最令人心碎悲慟的日常。此外,當中許多因戰事爆發之初被迫逃離至鄰近國家的老弱婦孺,這段期間已逐漸返回家園。中央政府班師回朝,坐鎮首都,大部分外交領事單位也重啟門戶。近日來,歐洲國家的領導人紛紛前來訪問基輔,無疑是「國際支持」的重要表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