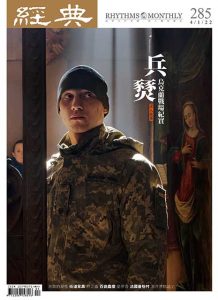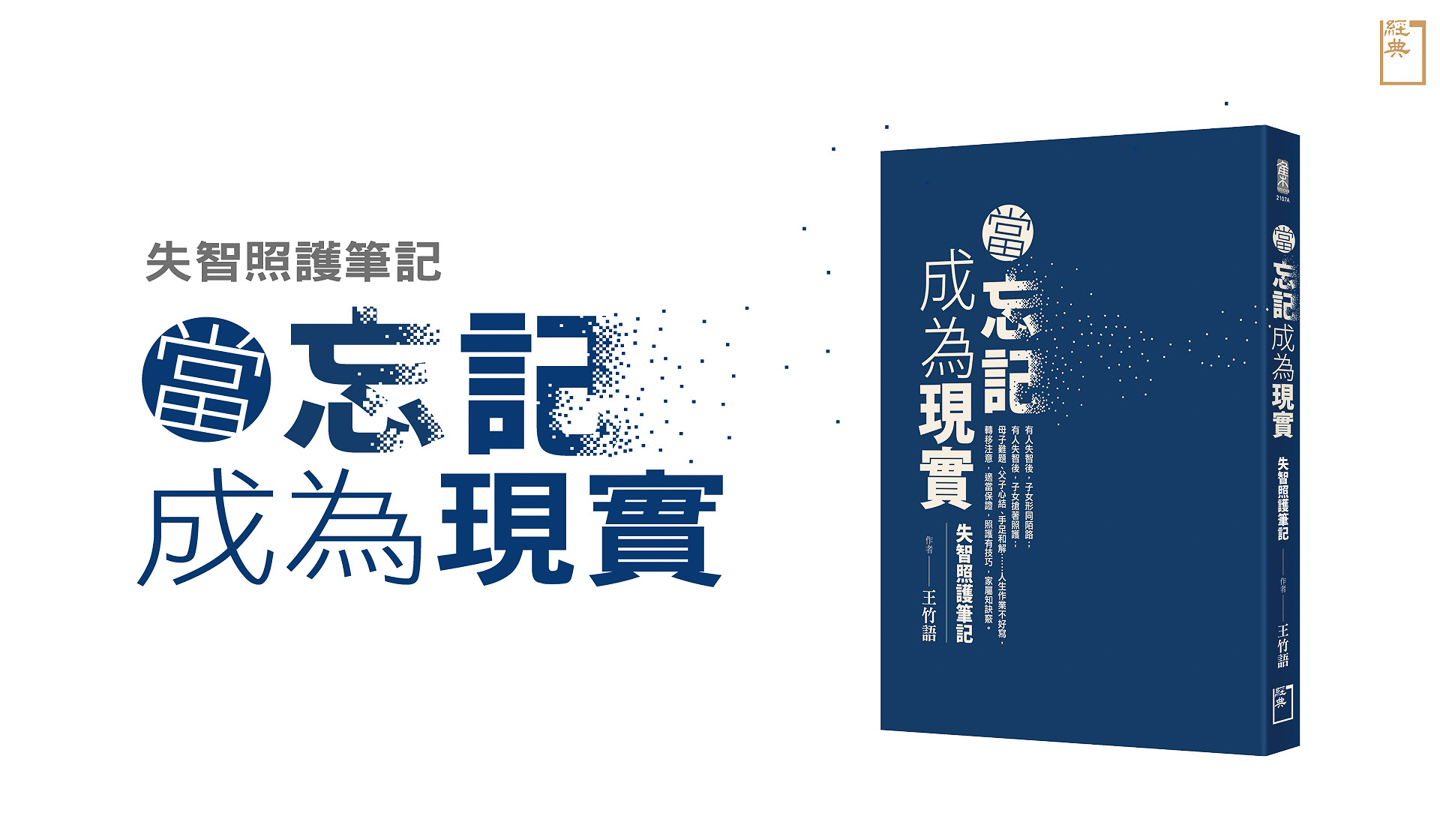凌晨三點,微涼山風挾帶濃濃雨霧籠罩全城,是個適合賴床補眠的溼冷天,新北石碇潭邊村「竹柏苑」的工寮則如常飄起了炊煙。負責人王宏健將鮮採的小麥草絞碎成泥,一邊生火起灶,將預先泡了一晚的糯米入鍋蒸熟,接著生火燒柴,然後將熟糯米、小麥草泥、石碇山泉水入鍋熬煮。春天後母面,凌晨寒氣濃重,他卻熱得打起赤膊,臉龐因勞動頻密冒出陣陣油光:「煮麥芽要不時翻動攪拌,讓水分均勻蒸發,到後來會愈煮愈稠,更要緊盯著,不能巴鍋。」柴火滾煮、燄苗高竄,再過數小時,麥芽、糯米就會糖化成琥珀色的麥芽膏,香甜Q軟不黏牙,單吃或料理調味,兩皆相宜。
人類「呷甜」歷史久遠,史前時期就有從蜂蜜、果實、蔬菜、穀物中攝取甜味的紀錄,西元前三百二十五年印度發現甘蔗、一七四七年德國發現甜菜,兩種作物蘊藏的蔗糖量高且易於大規模種植,遂成為二十世紀後製糖工業的主要糖源。台灣也曾是製糖大國。中國元代順帝至正九年(一三四九年)南昌人汪大淵著《島夷志略》談及琉球:「煮海水為鹽,釀蔗漿為酒。」
大多數研究者都認同此中所說的琉球,指的就是台灣,這份文獻紀錄足證台灣在十四世紀中葉便已經開始種植甘蔗,接著荷蘭人、日本人據台發展糖業,糖廠遍及全島,曾經興盛了數個城鎮、富裕了一整個國度。
然而,留在台灣人記憶深處難忘的糖滋味,卻往往不是用來料理調味或食品加工的蔗糖,而是街頭小食麥芽糖,或稱麥芽膏,以糯米、麥芽製成,相傳始於中國殷商時期,古稱「飴」,相較於量少價昂的蜂蜜與很晚才普及的蔗糖、楓糖等常見糖源,麥芽糖的發展早、技術成熟,雖然甜度僅蔗糖一半左右,但原料來自日常食糧,製作容易、美味又便宜。
台灣早期常有小販搖著「喀啦喀啦」的麥芽響鼓出現在村口、廟埕、菜市等人潮聚集地,應人客要求現場用長竹籤捲起一小坨麥芽膏棒棒糖,有時包著話梅,或夾入兩片餅乾做成麥芽餅,沒錢買的話,也能拿空酒瓶、奶粉罐、舊鍋等「破銅爛鐵」通融換得,在那個「酒矸倘賣嘸」盛行、回收品尚有經濟價值的年代,即便是窮人家,嚐到一口珍貴幸福的麥芽甜香也並不太難。
麥芽膏製作簡單,只需三種原料:小麥草、糯米、水。製作卻十分費工:小麥草怕晒怕高溫,得種在攝氏二十至二十三度的暗室,溫度一上升就要趕快開冷氣送涼。「人再熱都沒關係,但小麥草過熱會轉綠、味道變苦,就前功盡棄了。」小麥草要在約莫一星期長到三至五公分高,鮮黃色、酵素含量最高時採收,攪碎拌入蒸熟的糯米混合發酵數小時,放入大鍋熬煮又是數小時,時間長短視天候而定,夏天短些,約四至五小時,冬天熬上六至八小時也是常有的,然後濾掉渣籽,再將剩下的水分繼續小火熬煮濃縮收乾,就是「一番搾」的原生麥芽膏。
麥芽膏的甜來自酵素(小麥草)與澱粉(糯米)兩種天然穀物發酵產生的還原葡萄糖。「就像白米飯放在嘴裡慢慢嚼,人的口水(酵素)混合米飯(澱粉)發酵,會自然產生甜味的道理是一樣的,這就是自然糖化。麥芽膏並不是麥芽糖。」王宏健對於很多人對麥芽膏一知半解很無奈:「常有客人說血糖高不能吃麥芽糖,但是,正港循古法製作的麥芽膏是不含蔗糖成分的,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宣導的事。」
歷經數小時的火燒滾煮翻拌,小麥草、糯米、清水,會自然糖化成琥珀色的麥芽膏。